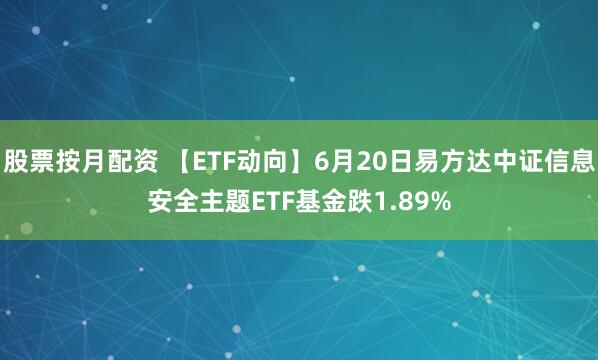二刷丁蜀,文思已尽。
同行皆文章高手,迫不得已改一个思路,从自己较为擅长的城镇研究入手,来观察一下丁蜀的规划思路和城镇形态。
悠长的蠡河边,我的对面坐着伍震球镇长。他是学规划出身,又是本地人,以土为念的思想很强烈,长期在丁蜀工作,见证了丁蜀近十年来历史文化建设发展的历程。
每个有特色的城市和街镇,其实都有自己可辨识的独特意象。比如北京的故宫天安门,上海的外滩城隍庙,凯文·林奇将之定义成一座城市的“可读性”和“可意向性”。那么,说起丁蜀又会想起什么呢,无疑是一把紫砂壶,如果要说出丁蜀的三个意象,有人斩钉截铁地回答:紫砂、紫砂,还是紫砂。可见紫砂于丁蜀是多么让人“上头”。
探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是一个大话题,全国3000多座古镇如何规划、设计和营造,如何避免“一条河、一条街”的单调模式,既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,也是一个长期主义的问题。无论是宏村,还是大研,尤其是乌镇等江浙一带的小镇竖立了很多成功的样板,上海水乡古镇也在奋起直追。但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,留下一条迁走原住民,而又无法吸引到足量游客的古街,绑着一条需要人工放水的笔直河浜,甚至没有古街也要建一条仿古街,“同质化”倾向和贫乏的审美严重侵蚀着当下的城镇建设。
丁蜀的城镇规划已经做得很好,因为热爱而投入,因为熟稔而自信的伍镇侃侃而谈(以下以“伍”和“徐”代表主谈者和与谈者):
伍:丁蜀从大的规划设想来说,还是想往更高的一些目标去努力,比如申报联合国人居环境奖和联合国文化遗产,我们并不是一定需要这些名头,而是想以此激励自己,作为一个导向,把文化、城市建设,还有民生等实际已经开展的工作结合起来。丁蜀还有很多需要更新的老旧小区,不能光搞些通道景点。
徐:现在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有个倾向,就是喜欢用游客的眼光看城市,而较少考虑当地居民的需求,你不能说它错,但两边还是要平衡好。我有一次到潮汕,发现它的非遗不停留在文创产品上,还有原汁原味的实体,在乡下很红火。古城中心有一条主商业街,适合网红打卡,但周边照样居住居民,这个模式挺好,不像有些地方就搞一条古街,旁边居民全没了,空空荡荡。那边居民还是在周围生活着,但生活区和主街又紧紧连在一起。
伍:这几年的建设,我们没有搞布景化。我们的出发点是“生活优于旅游”,生产生活不分,生活的场所和文化的场所也不分,景点同时也是一种生活场景,这样更高级,更符合未来融合多元的趋势。我们将陶文化旅游目的地、5A级景区、人居环境示范和文化遗产的目标叠加在一起,规划总的脚就立住了,规划还是要志存高远,但更要做好每时每刻的基础功课。第二是城市的能级,我们不可能做得很大,但还是要略微做一些扩展。因为你还是要人口的基数,为了后面发展三产服务业,我们现在定的目标是25万,最好能够做到30万。要可持续发展,人文的背后就离不开经济。包括紫砂行业,也要有危机意识。
紫砂已经“功成名就”,但在紫砂行业逐渐萎缩的情况下,能否让陶都有更多兴奋点,或者套用网红时代的术语,有更多“新皮肤”,则是不墨守成规的创新开拓者需要前瞻考虑的问题,除了紫砂,丁蜀其实还是个太湖边上的“山水小镇”。
徐:围绕紫砂意象,将街道融入到山水之间,打造一个以陶文化为内核的山水小镇,将陶都之旅变成全域旅游,成为未来中国小镇建设的一个样本和范式。丁蜀有什么想法吗?
同行考察者的忧虑,其实已在丁蜀治理者的考虑之中。他们已经在扶持“五朵金花”中的均陶和青瓷,已经在考虑“陶山轴”和“陶水轴”的布局。
伍:第三是城市的架构。和你讲的一模一样,我们今后重点要打造两条主线,一条是陶文化的山轴,一条是陶文化的水轴。从蜀山、黄龙山、青龙山,一直到丁山大河,山水相依,人陶共生。以紫砂为核心,但是它整个展现的是一个山水小镇,具体的方法就是串珠成链。大部分的地方,就是画一个圈圈把人赶走,我们的三期改造是把时间空间都整合集成在一起,用长期主义来一个点一个点慢慢打造。
徐:讲到比较技术性的问题,针对游客的旅游产品设计、动线设计其实也很重要,就是你讲的这个串珠成链。可以搞一个“丁蜀Citywalk”,把一个个点设计好,在多少时间里玩得体验最好,性价比最高,人性化、精细化地考虑到包括上厕所等问题,其实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。
伍:你讲得非常对。哪些地方可以步行,哪些地方有自行车、小黄车,有些地方可以公交,要做得很具体,然后每一段要有一些惊喜。这个地方转角有一个小雕塑,一个小店,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景,一个卡位,可以拍个照。后面肯定要一段一段来专门策划设计,比如说刚才从陶二厂走到古南街,如何让大家惊喜连连。对于旅游者来说,走上一段可能是喜悦,但是时间长了,喜悦也可能变成痛苦。看景点,你不能一直看茶壶,最开始可能很喜欢看,到后来就觉得重复了。看了一段时间后,可能要换一个频道了,那就看均陶。沿着这条河,蜀山是紫砂,中间是均陶,西面是青瓷。
徐:节奏感很重要。消费者有不同层次,现在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一个“含青量”,就是让年轻人喜欢,没有“含青量”的项目,将来前途不大。您怎么看?
伍:对,年轻时尚还是主打。刚才看的陶二厂,是在原来紫砂二厂的基础上打造出来的,由邀请隈研吾设计的UCCA陶美术馆,以及俞挺“烧制”的陶书局,包括“谷子店”组成,“含青量”很高,吸引了不少Z世代二次元的年轻人来打卡。除了年轻人,还有银发经济、甜蜜经济。年纪大的人,许多人还有一颗年轻的心,客群是需要细分的。
徐:60岁到75岁,现在定义叫活力老人,按照日本的标准还不算老人,刚退休的年纪还只能算“准老人”。现在社会上最活跃的就是这批“生龙活虎”的“老人”。
伍:实际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思路了,你上次来看到的成人学校,老师培训,DIY做壶,客人住在丁蜀,不仅看风景,还可以参加很多沉浸式的文化活动。如果上海有一千、几千个你刚才讲的活力老人,喜欢文艺的在这边常住,那就不得了了,慢慢沉淀下来,对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发展肯定有帮助,而且来了以后要交流,要碰撞。
徐:碰撞就会产生粘性,人来了,产业自然也来了。现在网红流行,网红有好处,起码帮你做了一波推广,还有对地方的治理短板也是个检验,但寄希望于热闹一阵的网红长久拉动地方消费,其实并不靠谱。
伍:需要热闹,但不能一直沉浸在网红里面,做长远还是要有文化。我们后面有个特别针对年轻陶艺家的孵化器计划,我们免费提供房子,提供师傅。每年给长三角的艺术学校提供10个、20个或者50个名额,精准的把喜欢陶瓷的年轻人找出来,吸引他们来丁蜀。慢慢的,同学、亲戚、朋友都过来,在这边创作生活,再结合世界陶艺家驻留计划,相互之间产生碰撞,丁蜀就会变成长三角、上海大都市圈里面的一个陶瓷文创集中地。如果最终有一两万人长期居住下来做陶瓷,体量一上来,别人就不可能跟我们竞争。因为你没有这个产业链,泥从哪里找?工具从哪里找?去哪里烧?如何包装销售?旅游者是流动的,但如果两万人住在这里,要租房,甚至最后要买房子,配套就全部带动起来了。
徐:您将“陶文化”改成“陶文旅”,一字之改,境界全出。其他地方可能还不能说,但在丁蜀,文化就是经济,互为体用。
伍:我的理解,陶文化是内功,陶文旅是招式,就像天龙八部里的段誉,内功虽强,招式不行,也不行。文化还是需要产业支撑。我们的最终目标,是要实现城市、产业、文化、生态和民生五位一体的均衡发展。现在,丁蜀目标、方向、定位、架构,包括打造的方法措施都已明确,只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。
我发现,我说的伍镇都知道,只是验证一下而已,而且理解得更深入,不禁相视而笑。实践出真知,作为一个实操者,伍镇可以讲得更接地气更明白。
伍:具体落实是“一三七”。一是一条陶文化主题游径,目前还是1.0版本。紫砂从什么地方来,到什么地方去?讲清楚紫砂的前世今生,通过打造“泥、窑、水、火”的空间,让游客实地感知陶文化。三就是三个传统节日,我们把陶文化和在地文化、传统文化进行一个整合。第一个节日是端午,端午赛龙舟,在南方是一个喜闻乐见的群众运动,参与度特别高,老百姓喜爱。我们把龙舟看作是一根针,从西面的小窑墩一路过来,经过莲花荡、古南街、青龙河,把陶文化的历史空间串联起来,形成了水轴。第二个节日是中秋,主要围绕蜀山东坡文化,去年搞了一个论坛,由国家文旅局牵头,和我们文物局一起搞了东坡主题游,我们自己搞了东坡明月集,和陶文化结合,和蜀山市集结合,走老百姓的路线,沉浸式体验,有点如在宋朝的味道。第三个节日就是春节,年初五我们搞龙窑过大年,因为初五是迎财神,过大年开窑意味着丰收。七就是七个郊野公园,我们不是刻意去打造,结合这几年新农村建设,高标准农田建设,太湖美丽河湖建设,我们把散落在镇区的现成历史点位进行整合,归纳出了七个郊野公园:太湖绿道、上坝、乌峰岭、大潮山、莲花荡、光明小镇和洛涧。每个郊野公园功能都不一样,有些是郊野爬山,有些是水上活动,有些是农耕文化,有些是乡贤文化。我们没有浪费任何一样东西,也没有把任何一样东西做成一个盆景。
今年陶文旅起来之后,大家觉得丁蜀是一方热土,营商环境好,今年餐饮住宿都起来了,本地老百姓的就业率也在逐步上去。
在滔滔不绝的默契互诉中,我们找到了强烈的共识。丁蜀的“大规划”和“一三七”思路,陶文化与陶文旅互为体用,以“泥窑水火”为场景,非遗节日为“活态”,瞄准目标客群,沿“陶山轴”和“陶水轴”设计旅游动线,以及七个郊野公园串珠成链的实践,和我们这群访问者对丁蜀的畅想非常契合。因为有一批守土而坚韧的治理者,丁蜀其实已经做得很好,留给我们的,只有敬佩和祝福。
形制特别的横窗外,绿意酩酊。在春山在望酒店,在茶叶研究所,在吴冠南艺术馆,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扇符号性很强的“绿色横窗”。光影下,绵长的蠡河悠悠荡荡流向太湖。
丁蜀,正像中国小城镇发展的一扇“横窗”免费配资系统,让我们在经济发展中看到了坚强的绿意。
恒正网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